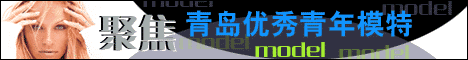孔夫子并不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人。如果你用心倾听,就会发现有一种美妙而舒缓的音乐贯穿于《论语》之中。孔夫子的“乐”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器乐、舞蹈和诗歌等等。孔夫子虽然把“乐”列为六艺之一,但是,他并没有把“乐”当作单纯的一门技艺、一种艺术形式,在他看来,“乐”是一种完整的生活、一种生存方式。
孔夫子沉浸在音乐生活中不能自拔,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这不仅仅证明他的美感极为灵敏,情感极为投入,也充分表明了孔夫子重精神轻物质的生活态度。音乐是一种没有明确指向的语言,她只是启发、暗示,却从来都不强求。钱穆在《论语新解》中称孔夫子的这种迷醉为“此乃圣人一种艺术心情也”。我认为,在音乐世界漫步的夫子还不是什么“圣人”,齐国的韶乐也不是什么圣乐,一切都是平民化的,音乐不分等级和贵贱,音乐消解话语霸权。所谓的艺术心情实质上就是一种对生活的审美感悟,在这里,音乐与生活融为一体,音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音乐。
后世的解释者都清楚“三月不知肉味”中的“三月”是“言其久也”,但是,却总是在有意无意之中,理解为孔夫子的这种痴迷不过是某个时间段的心理作用。我却认为,孔夫子的“不知肉味”是没有时间下限的。音乐是一个过程,烦躁而匆忙的奔赴于一个又一个目标的人是无心去听什么音乐的。音乐生活是一种和谐的生活,也是一种超脱的生活。乐以忘忧的孔夫子追求的是一种音乐的化境。充溢着音乐的心情平静如水,柔和而又坚硬地将世俗的东西挡在了外面。瞬间的感悟与绵延的梦想交融在一起。孔夫子对世界的认知不是从死背书本出发的。《诗经》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当然,孔夫子所做的不仅仅是配乐谱的工作,他动情歌唱的情景我们已难以想象。因为后世的儒生大都干瘪而无生气,全然没有了夫子那般旺盛的诗情。虽然儒生们大都会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那一段,但是,他们已达不到“咏而归”的高峰体验了。在孔夫子时代,诗云子曰并不是什么死板的教条,也不是活学活用的万能语录。我甚至认为,孔夫子对语言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巧言令色的人是为夫子所不齿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音乐则是有意味的形式,是不费口舌的语言,是充满隐喻的言说。孔夫子通过音乐接触到了自我以及世界的本质,所有的智慧、情感和理性都在音乐里面得以实现。可见,音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心怀鬼胎的人是没有资格面对音乐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生活包容了一切。音乐是和谐,是平衡,也是人格修养的外现。孔夫子清楚,所谓的人生哲学其实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要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完善自己,这个过程不可生硬、不可机械,要像音乐那样缓缓流淌。孔夫子的生活不但“依于仁”,而且还要“游于艺”。李泽厚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舞’、‘乐’,是‘变’,不是‘在’,它没有对象化为一个外在的世界,就在过程中间”(《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谈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与艺术》)。孔夫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把现实功利转化为审美追求,把对立冲突转换为天人合一。孔夫子不是单纯地听音乐,《论语·述而》言:“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夫子是十分讲究“和”的,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交流对话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音乐的美是抽象的,是虚幻的,这决定了音乐生活的自由本质。音乐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悦耳,而是给人提供一个和谐的心灵空间。没有了音乐,也就没有了思与梦的自由,心灵的秩序也就会发生紊乱。“礼崩乐坏”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由的丧失。像杨朱那般“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看似痛快,实质上成了欲望的奴隶。经过音乐陶冶的人是不会用这种掠夺的方式来经营人生的。
音乐是来自灵魂的一种召唤,它促使那些“在路上”的飘泊者永远都不停止脚步。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人在痛苦和绝望之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往音乐”,那是一片心灵的净土。而我们的孔夫子却是快乐着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