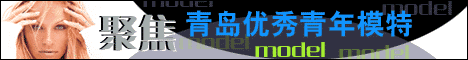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死亡的细胞,背叛我们的身体,皮肤塌陷成皱纹,像死亡贴上去的通知书。但除了这些生物意义上的体验,我还感到我曾经沸腾的血液温度一年比一年低,我对曾经热爱的事物兴趣也越来越少,我不再有新的理想,我不再为什么事情激动,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更有意义的……当我在米尔博笔下找到一个知音,我这才意识到,我正同时以两种方式在进行我的死亡。那是世界上最彻底的死亡。
神经衰弱者在疗养的最后一天去一个小村庄看他的朋友罗歇。这是一个曾经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但当他猛然想到死亡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所做的努力是多么渺小和虚浮,“艺术是一种堕落”,“文学是一种谎言”,“哲学是一种故弄玄虚”,人在这种努力中愚蠢地消耗着生命,因此,他希望在远离都市、相对纯净的乡村寻找一种人,从他们身上可以发掘出美来。但他失望地发现,所有的人,不管他干什么,都在走向死亡。于是他永远地留了下来,留在这死去了什么东西的寂静之中。神经衰弱者问他为什么不自杀,他平静地说道:“人们是不会去杀已经死了的东西的。”
深感震惊的神经衰弱者决定离开温泉城,让导游带他回到人群、生活和光明中。
深感震惊的还有把《一个神经衰弱者的二十一天》阅读到最后的我。头一次,我不是被语重心长的教导而是被一种深深的绝望所震动。当然,这当中的前提是绝望者是清醒的,我同样是清醒的。
清醒也许意味着希望,有谁跟光明过不去呢?孩子的脸为什么可爱?纯净,快乐,像朝阳的花朵。没有人喜欢灰色的人,不管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不喜欢米尔博笔下的罗歇,我才懂得有的朋友为什么不喜欢我的沉闷忧郁。我理解和感谢这样的朋友。人们都喜欢积极向上的人,快乐的人,但罗歇却说这是“更快、更自觉地走向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瓦解过他,正在瓦解我的东西是死亡。
仔细地想,死亡既然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共同的结局,那么剩下的东西只有千奇百怪的过程了,罗歇是被死亡巨大的阴影遮蔽了,而一切快乐的人都是看不见远处的死亡的人,不去想象死亡,或者说只用一种不可抗拒的生物方式走向死亡,而他们的精神永远年轻。我深深记得这样的镜头: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走路踢易拉罐;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还喜欢跳舞、放鞭炮。也许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像年轻人一样约会谈恋爱。这是多么令人惊喜和羡慕的事情。他们只有死去的细胞,而没有死去的精神。
浑浑噩噩、没有激情的生活不是什么美好的感受,我们抗拒肉体的死亡,却往往忘记与灵魂上死去的东西做斗争,我很想知道这些东西怎样才会不死,它们有些存在于一个人的天性中,问题就简单了,有些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中,是很容易丢失的。但我知道答案就能挽救那些死去的东西吗?毕竟,它们也受天性的左右。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身体的一半死亡由物质规律决定,而另一半死亡由我们的意识决定。我们要做的事其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