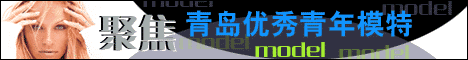我好像是突然听到了雨声的,那声音微小空茫,又扑朔迷离,我能感觉到大地从我的长沙发底下延伸到天边,天边烟雨蒙蒙,雨声大约就是从那极遥远的地方飘过来,像是谁无意间弄响了这个世界。
其实,这个世界原本是没有声音的,由于拥有了雨声,它才有了生长的声音,以及生灵们的欢歌与哭泣。其实,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声音的,自从人类诞生并选择了此处栖息,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厮打与喧嚣。历经了雨的冲洗之后,世界能否恢复其原本的单纯之美呢?然而,不管结果会是怎样,雨声总是令我感慨万分的。春雨,往往就是这样悄然而至,不像夏秋时节的雨给人一种发泄或毁灭般的感觉。由此,我会在如此缠绵的雨中,回到一片空旷而寂静的地带,雨水浇灭了我积蓄已久的火气和忧虑。我走在雨中,天地中间扁平如隙,它们与云层、田野及躺在长沙发中的那个我,同处在一个横向的队列中。于是,我听到了雄壮的节奏中有一种独特的声音传来,那是一种陌生的,崭新的,带着异域情调的生长之声。我看见了,我的窗下的那一小丛黄杨,直立着,与整个大地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直角。那一丛黄杨,低矮、蓬头垢面,非常认真地接受着雨的洗礼。
一天下午,当我钻出昏暗的楼道,便望见了我的窗下种植上了一小丛植物,起初我并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它们的样子很稚嫩,椭圆形的叶片显得十分厚实,枝叶里面夹杂着刚滋长的鹅黄色的新叶。枝头有被剪断的痕迹,粗糙的树皮上渍着泥土,那泥土湿黑,里面还有草屑。黄杨像一个部落似地安扎在我的窗下,周围是高楼大厦。我茫然四顾,问种树的男人:“这是什么树?”他说:“黄杨。”
黄杨!平原的黄杨!低矮得就仿佛匍匐在地面上一样,它们带着别离故土的忧伤和憔悴,它们还弱不禁风,还心存对都市的畏惧。我从它们身边走过,我想,它们能否坚定信念地在这里活下去?这里没有河水,没有庄稼的围拢,没有蝴蝶和鸟的飞舞。这里肯定有不屑一顾的冷漠,有无意有意的破坏,有对于它们生长的限定等等。黄杨是不会长高的,它们是要被不断地修剪的,它们充其量就长到一层楼的窗台下边,它们永远都需要我走近它们,俯视并怜悯它们。过去,我在那座山城的时候,我家窗外的那棵大杨树仿佛一个夜晚就长到了窗下,又一个夜晚,就长过了晾台。我眼看着它,从一楼长到了五楼。那是怎样的夜晚,大杨树呼叫着生长。在我的感觉里面,树的生长永远有着江河流淌般的速度与力量。
难以想象的是,如今我的窗前,竟然种的是一丛黄杨,一丛与我记忆之树的长势反差极大的树,一丛不会长过窗台的树,一丛或许你一生都不会惊叹其生长的树,我有些悲哀,我真的不希望是黄杨而是其它任何一个树种的树,种在我的窗外。或许我害怕天天面对毫无突破性成长的树,我的心智会衰竭。而我的心智衰竭的时刻,迟早要到来的。然而目前,我依旧感到了幸福。许多年了,我的窗外没有树,什么树都没有。许多年了,我走到窗前,一眼望去,是一大片红色的平房屋脊。后来平房都拆除了,屋脊们鸟群似的飞了却不再归来……雨下着,下得无声无息,我需要走到窗前望着雨,确认一下雨确实是在下着。雨飘过来,扑到了我的窗玻璃上。玻璃上的雨转瞬就变成了一滩滩的水,然后顺着玻璃往下流去。透过窗户,外面的雨下得幻影绰绰,我看见雨中的黄杨伸展开了枝叶,树皮上的泥土被冲掉了,鹅黄色的新叶骤然间多了起来,或许就是在此刻黄杨刚又滋生出了新的嫩芽。群居的黄杨在雨中跳荡着,它们甚至逃离了泥土在半空蔓延开来,或许黄杨只有借助着雨,才可以将自己沉默的坚韧与宽容,飘洒在四面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