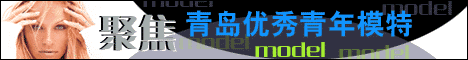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文学可分二项: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
读此颇有疑。又往下读:“你看,动物中不能言语,他们专以幽美的声调传达彼等的感情,可见诗是必要有韵的。”前面的是观点,这儿的就是论证了,然而其论证却让人哭笑不得,是无理。
在该书的附录、曹聚仁的致章太炎信中找到了知音:“聚仁窃以为诗与文之分以有韵无韵为准,恐非平允之论。韵者诗之表,犹妇人之衣裙也。以妇人之衣裙加于妇人之身,曰是妇人也,诚妇人也;若以妇人之衣裙加于男者之身,而亦谓之为妇人,宁有斯理乎?《百家姓》四字为句,逢偶押韵,先生亦将名之为诗乎?是故诗与文之不同,不在形式,精神上自有不可混淆者在。”
曹氏把诗的特质核定为“言志”,认为文只是用来敷陈事实。不管这恰当与否,比之章氏之论,是有质的飞跃的。
章氏失足于诗与文的分水,与他对白话文、白话诗的成见是分不开的。他认为近代白话诗是诗的“堕落”,并且极具嘲弄性地给白话诗找了个始祖,即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
新事物的诞生总是要对旧事物有所扬弃的,白话诗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难免手忙脚乱,捉襟见肘,丢三落四,这样说,章氏之论是有道理的,只可惜他没向远处看看,没向本质处瞧瞧。白话诗文是新时代的要求,是无论什么硕儒大师都抗拒不了的历史的要求,是人性的要求。章氏优悠生活于书斋之中,思考于故纸堆之中,要是能伏下身子研究一下民间风雨声,要是能探出耳朵倾听一下新生活的钟声,怕就不会反感白话诗文了吧。
既对白话诗文嗤之以鼻,章氏有文学前途悲观论也不难理解了。在《国学概论》最后,他说:“在现在有情既少,益以无义,文学衰堕极了。我们若要求进步,在今日非从‘发情止义’下手不可。能发情止义,虽不必有超过古人之望,但诗或可超过宋以下诸诗家,文或可超过清以下诸文家!”
应该说,如没有民国和新中国,如清后还有一个封建王朝,章氏之论会是了不起的极具深识的大论宏论至论,即使今天,我们若撇开时代因素,专从文体、文本去作静态考索,“发情止义”的提示概括也是相当精辟的论断。
只可惜,文学之事,常常是由时代来作最后结论的。
章氏对欧西哲学也持轻视态度,难怪邵力子会说他“恶新”。
在新旧交替的当时,章氏贬薄白话诗文与欧西哲学,是对学术的歪曲,是知识的倒退,是历史前进中的障碍石,对新青年成长自然极有害。
《国学概论》中没讲史学,也没提医学、军事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只讲了经、哲、文,“经”相当于政治学和社会学。
我们现在讲国学,怕不会遗漏这么多吧。
对于道德人情,章氏又极开通。《国学概论》中把“道德”分成普通伦理和社会道德两部分,认为人情风俗也应随社会更迭变换而变迁,而道学先生把道德视为永久不变,把古人的道德,比作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墨守而不敢违背,则是大谬。
章氏此论让人耳目一新。想《孝经》中原本提倡的健康的孝道,被后世演变为变态的孝道,又想古代好好的“礼”发展为后来的繁文缛节、虚与委蛇,真让人感慨。
章氏也认为颜回是庄子老师,这与郭沫若观点同;他论孟子不及荀子博大通明,也极是;论庄子的自由平等,也很平易;论李杜难分伯仲,也合公论;论更始刮席与呆子王莽,也算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