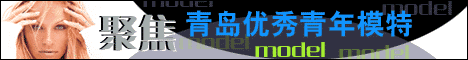我从来没有在书里,在有关收集民间歌谣方面的书里,或者在记载那段历史的书里,看到过这首歌谣。我相信,相对于漫长深厚的历史,所有记叙它的文字都不过是岁月的一种遗漏。可以说,曾经发生的几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声音,所有的细节在其发生的同时就已经亡失,更何况,残存的真实记忆也是不许说出口的;到了可以说的时候,又不想说了。它们被永远地带走了。这样看来,一百多年前写在倾圮的墙壁上的这首几十个字的歌谣,今天由我再一次写下来,是一百年前的那个作者和一百年后的我所想不到的。
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谣是母亲背给我听的,她说这是她的母亲我的姥姥在一面墙壁上亲眼所见。后来,在我的一个表哥的笔记本里我又看到了这首歌谣。他给这首无名的歌谣起了个题目,叫作“祖母教给我的歌”。这个题目证实了歌谣的来源的确是我的姥姥。同时也表明了她对这首歌谣某种认同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也是我表哥的倾向。那是六十年代初,我的表哥正在一所有名的学校里读书。他才华横溢,迷恋着文学,经常发表诗作。他能够这样优美地写离别:
“浮萍随着流水去了,托着晶莹的泪珠———”
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学生时代应该是他唯一的幸福时光。我不知道,他是怀着一种怎样的感受在这样一个题目下记录了这首歌谣,也许是生活已经让他对歌谣的内涵有所体察。其时,他的祖母,他的母亲,他的父亲,都已经离世。关于我的表哥,他的一生的经历,可以拍成一部耐人寻味的电影。只是这部电影没有故事,没有悬念,没有爱情,也没有显明的主旨,它的全部内容只是一些粗糙不堪的细节,也许,会有一些温馨的片断,但也模糊不清。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他经历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他与所有认识他的人断绝了音信。后来我在一个小城镇见到了他。他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他已成了一个占卜者,一个年老的占卜者。
这就是那首歌谣:“荒荒世界乱如麻,自己跌倒自己爬。要人拉,得酒饭茶。平日交了些好朋友,有了难事去找他———他不在家。”
相比今天的民谣,它也许显得有些温和。可我要说的是,这首一百多年前的歌谣,是我的姥姥在她家乡的一堵残破的山墙上看到的。当时,正闹义和团。我的姥姥还是一个少女。那是在一次躲乱的时候,当喊杀声,马的嘶叫声,大刀长矛的碰击声和其他别的声音都归于沉寂之后,我姥姥走出了藏身之处,她说在一片硝烟和血腥的气味中,她看到了那个正在写歌谣的人。那是一个义和团的战士,是一个中年人。空荡荡的村庄在那一时刻里好像只有他一个人。他满脸胡髭,身穿白色的袍子,又脏又破。他用一支毛笔在一面被毁掉了一半的山墙上写着,写完之后,他把笔向地上一摔,就撵他的同伙去了。他写的就是这首歌谣。
我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困惑不解:这个刚刚参与了洗劫的义和拳为什么不写一些扶清灭洋之类气壮山河的口号。我隐隐感到,在这个真实的场景里,在这首歌谣之外,有某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它是属于这个中年人个人的,它在他的内心存留已久———这个穿白袍子的人大概算是那个时代有文化的人了。对于这个参加战斗已嫌年龄太大的乡间普通知识分子来说,时时置身于焚毁残杀流血死亡之中,他的心灵生活究竟怎样,我们无从得知。可是,他用家常话一样的语言写下的这首歌谣,却说尽了人间发生的一切冷漠,说尽了人生处于无助之中的全部辛酸。这一定是他从长期生活中获得的最大哀痛。这首歌谣不是宣传,也不是鼓动,它是完全私人化了的一种愤懑,一种诉说,一种表白。他是在说他非常无奈,他只有铤而走险。这个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个人的生活伤痕走进了这首歌谣,我每一次都能够在这歌谣里看到他。这不是民谣,这是属于他个人的歌。
过去了一百多年,这歌谣竟然没有蒙上一点儿历史的灰尘。我还记得,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听这歌谣时内心的某种领受。我的母亲,我现在知道,她当时所处的生活境地即使一个强壮的男人也是难以承受的。向着一个年幼的孩子背诵这样的歌谣,是孤立无援的母亲发出的一种叹息。可是,在我作为孩子的有限想象空间里,我过早地接触到了未来存在着的那种不可接受却又必然要来临的东西。这一切,当时在我的心里只能通过歌词所描绘的图画加以完成。这样,我即时的体验就永远是一种惆怅。
“有了难事去找他———他不在家。”
我的感情关注全部都放在这句话上,我觉得,事情并没有完结,还应该再发生些什么。从那时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这不是最后的一句,这不应该是最后一句。事情没有完结,不应该就这样完结。怎么能这样就完结了呢?
这首歌谣无疑在那个少女心里产生了震动。她记得是这样真切。她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只一次地讲给她的女儿听讲给她的孙子听。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和我的姥姥生活过一些日子。我的姥姥最后是被饿死的。当时,没有人帮她,没有人能够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