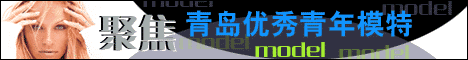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最早认识崔健,就是从这支歌开始的。他用简简单单的歌词和轰轰烈烈的节奏,唱出了那个年代隐隐约约的尴尬。我曾经对崔健有着深深的误解,很多年来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挺不错的摇滚歌星。而我又偏偏没有追星癖,始终保持着和所有“星”的距离。这使得我在很多年里一直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着的那只眼还是冷眼)的态度对待崔健。我知道崔健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他的狂热的追星族,我还知道崔健就像一位催眠大师,走到哪里哪里的观众就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疯狂不已,我只把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类为追星族的集体无意识,当年全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天南海北,不也曾集体无意识地痉挛过么。当我们这一代人的激情被掏空以后,现在再看看年轻一代追星族的狂热,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无限感慨。
前不久崔健来到天津,一位朋友兴致勃勃地送我一张崔健演唱会的票,我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有去。
我还有那份激情么?
可是很快我就后悔了。一位在饭桌上刚刚认识的朋友向我朗诵的崔健的一首歌词深深地攫住了我。我被崔健的深邃击中了。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那些日子里,我近乎热恋般苦苦地追寻着所有有关崔健的CD。几乎所有的店家都摇着头告诉我:“崔健早已过时了。”我不明白,崔健怎么过时了呢?崔健怎么能够过时呢?后来我终于如获至宝地从一个小贩那里找到崔健演唱会的影碟,不顾小贩的狠宰一刀,用高价把它买了下来。
我终于拥有了崔健的摇滚,我终于静静地沉醉在崔健的狂热中。
其实,我们误解了崔健。他并不是一个歌星,因为你无法把他归类到歌星当中去,如果那样的话对其他歌星就不公平了。如果把崔健称作歌星的话,那其他人还能叫歌星吗?崔健也不是一个诗人,如果把他叫作诗人的话,那其他的诗人还好意思在文坛上混吗?准确地讲,崔健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只不过有的人在用笔墨记录着自己的思想,有的人在用行为诠释着自己的思想,而崔健在用他的摇滚抒发着他的思想。
崔健,一个让所有人无法安静的名字。老年人听了心律失常,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崔健比他们还要沧桑;中年人听了激情澎湃,在震耳欲聋的重金属般撞击声中,他们感觉到了生命的撕裂;青年人听了摇头晃脑,在剧烈的震撼和激烈的节奏中体味着欲望的宣泄;少男少女听了亢奋异常,反正哪个歌星都能击中他们的兴奋点。但是,那一张张年轻稚嫩的脸上分明写着茫然。
阳刚。壮美。节奏。眩晕。宣泄。还有那么一点点离经叛道……这些都是崔健。
但都是崔健的皮毛。
其实,崔健是需要静下心来,仔细地聆听,咀嚼,回味,和解构的。
他传递给我们的,是郁闷,是残酷,是错觉,是困兽,还有一点点黑色幽默。他袒露给我们的,是凝重,是严峻,是彻骨,是岁月沧桑。
和那颗沉甸甸的灵魂。崔健只属于少数人。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一个写家在完成一部吹捧崔健的书后却被崔健推上了法庭,因为他真的不懂崔健,崔健怎么能是他笔下的那个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呢?
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崔健会获得旨在奖励对世界各洲文化发展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克劳斯亲王最佳成就奖。
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谢冕先生在编《新文学大系》的时候一定要把崔健的两首歌词收进去。崔健的确当之无愧。因为他的思想穿越了音乐,穿越了文学,穿越了历史,他借着音乐的空灵,使自己沉重的思想努力挣扎在人类历史的上空。站在地上的我们只能感觉得到他的疲惫、无奈和绝望,却感觉不到他在飞。
是的,他一直在飞,尽管他常常说自己快要飞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