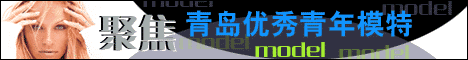长期以来,我不敢正视母亲的呆傻,更不敢向别人谈及自己的母亲,怕别人会因此看不起自己,影响自己的前途。
母亲3岁那年,一场重感冒几乎夺去了她年幼的生命;重感冒刚好,一名喝醉了酒的庸医又将活泼可爱的她治成了呆坐无语的弱智幼童。到了22岁那年,乡亲们都说母亲交上了好运,因为一位鳏居多年的老石匠看上了她。母亲受了无数的折磨,终于在两年后产下一子。数日后男婴夭折了。愤怒的石匠再次挥动铁锤,把母亲赶回了娘家。
一年后,又有媒人踏上门来,说的是我父亲家。
我们三姐弟都是在奶奶的怀抱中长大的。在我的记忆中,重新获得喂养权的母亲十分地爱我们。每次上山劳动,她都要翻山越岭寻找可吃的野果,用鲜嫩的桑叶给我们包回来。母亲看着我们吃“屈丝袍”野果的神情是我终身都难以忘记的———双眼微微地眯着,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这种微笑,也只有在纯真的儿童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踪影。
渐渐懂事的我们却不喜欢甚至怨恨母亲,因为母亲是个傻子。姐姐远嫁他乡,我当兵去了重庆,弟弟打工去了深圳。听父亲讲,母亲那时吃饭总要摆上我们的碗筷,总要到外面去唤一唤我们的小名。我们却不为所动,继续在外面闯荡着自己所谓的独立生活。甚至在别人谈及时,依然嚼着谎言说自己的母亲是一个修养颇深的知识女性。
去年11月,母亲下地干活,不小心脚趾被一块尖利的石头撞了一下,鲜血直流。不料数日后,伤口发炎了。县医院说是伤口感染引起败血症,让家里赶快准备后事。
当时的我,正在千里之外的军营里与报道员们谈笑风生,妄谈文学中的母爱。当我终于慢吞吞地赶回阔别7年的家时,眼前的情形却使我大吃一惊:家中灵堂高设,姐弟哭得两眼通红,母亲躺在棺木里,嘴眼不闭。我终于嚎啕大哭……弟弟默默递过来一张影迹模糊的照片,说是在母亲床前拾到的。这张照片是我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在新兵营的操场前留的第一张影。王宝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