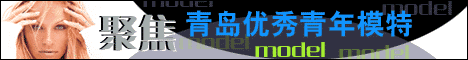周大学是从政法学院毕业分到我们这家县级法院的时候,院里没有几个正规政法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再加上,周大学身上有一股书卷气,满口都是法学术语,让我们这些半路出家凭经验办案的“土法官”感到一种新鲜感。因为他姓周,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周大学”,最早是刑庭的老杨庭长这么叫的。自从有了周大学,老杨头便有了军师和高参,每遇到疑难案件,他就喊“大学,你过来,给我们讲讲”。周大学于是一板一眼地给大家讲了起来,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从法理上讲”,尽管他讲的那些东西,我们在上业大的时候也学过,但是,毕竟是一知半解,不像周大学那样熟练,所以,庭里的同志不分年龄大小,都洗耳恭听。一开始院里也有人不知道这个“昵称”,径直喊周大学是“小周”,顿时招惹刑庭全体人员的攻击:“你才念了几年书啊!”言外之意是有志不在年高,无知妄活百岁。周大学并没有自恃才高而流露出傲气,他工作十分勤奋,除了办案,其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埋头读书上,大家伙儿越看他越像“大学”。大家说他不应该分配到这个小县城里来,到大城市、进大机关多舒服,周大学听后,淡淡一笑:“咱是庄户孩子,没关系没门子,老老实实干活儿就是了。”“大学”说话就这么实在,有好心人劝他不能光埋头干活不抬头看路,也有人对他说:“干脆甭入党了,当个民主人士,说不定提拔得更快!”周大学却说,他不愿意把心思用在琢磨人际关系和当官上面,他只想做个本本分分的法官。周大学很快就成了庭里的办案主力,难度大、关系复杂、被告人多的刑事案件总是由他来办,这并不全是因为别人没有这个水平,而是因为这些案子往往出力不讨好。不知周大学有没有看透同事们的这个小聪明,周大学总是心甘情愿地承办这些“烂鱼头”案子,他说,办那些简单案子有什么意思?周大学自有他的乐趣。周大学阅读案卷,像读小说一样入迷。一次,他审理一起跨地区盗窃黄牛的案件,涉及10多名被告人,作案上百起,检察院移交过来
的卷宗就有几十本,周大学整整读了3天。这期间没有人忍心打扰他,因为他实在是太专心了,一副沉思的模样。在伙房打饭的时候,周大学也在想案情,大家只好绕过他,悄悄地夹塞,以至于他常常打不上饭。周大学虽然如此敬业,但是却从来都不声张,在他的个人总结里面找不到“加班加点”、“废寝忘食”这样的词汇。所以,这么多年来,周大学除了“办案能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荣誉。这也怪周大学,他讲起案子来头头是道,争论起法律问题也是面红耳赤,脖子上鼓出青筋,可是让他汇报成绩什么的,他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满脸通红,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我们于是弄不明白,他到底是口才好还是口才差。
周大学遇到的麻烦事也不少。常常有一些当事人和他的亲属气势汹汹地到法院找“那个戴眼镜的”,同事们还没有楞过神,周大学便走过来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办的案子我负责”。同事们劝他有的当事人无理取闹,得寸进尺,完全可以不用理睬。而周大学却说:“我自有办法。”周大学的办法比较怪,他尽管让当事人把话说完,有的当事人嫌自己得到的赔偿太少,责任划分不公平等等,周大学也不多说,把有关的法律条文往那里一摆,你自己看好了,法律这么规定的,我有什么招?当事人见这一招不灵,便胡搅蛮缠,说一些漫无边际的话,哭哭啼啼地让人心里很不舒服。周大学并不厌烦,你说你的好了,他铺开稿纸,照样写他的审理报告不误。周大学的抗干扰能力确实让人佩服。他还不停地给当事人倒水,惟恐慢待了人家。等他说完了、哭够了,周大学便放下了手里的笔,平心静气地跟他攀谈起来:“你这个事儿,不能只讲一撇子理,你得先看看自己该担什么责任。”结果,来访者闹腾了一上午,让周大学几句话就说服了。周大学也有发火的时候。一次,一个被告人的亲属趁周大学不注意压在他的办公桌书本底下一摞钱,悄悄离开后,又打电话告诉周大学。同事们看见周大学气得手直发抖,怒吼:“你这是亵渎我的人格!”钱被周大学交到了纪检组,事后,同事们笑他何必那样激动,周大学说:“我最讨厌这些市侩!”周大学不好惹,这是许多当事人和律师都知道的,有的律师一听案子落到了周大学手里,便暗暗叫苦,他们清楚周大学是一个认“死理”的人,没有什么活动余地。有人千方百计托人请周大学“出来坐坐”,周大学总是不给面子,他的理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得小心吃了吐不出来”。需要交待的是,周大学1998年竞争上岗时,当上了刑庭的副庭长,去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亲切地称呼他:党员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