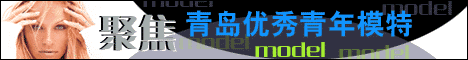1996年冬天,我在白雪的墓园送别了母亲,一枚沉甸甸的金戒指落在我手中,这是母亲留给我永久而惟一的纪念。我没有把它戴在手上,但我时常要把它找出来握在手里发一会呆,似乎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一年后,《一个神经衰弱者的二十一天》告诉我一个铁戒指的故事,这枚铁戒指搅动了我久已沉淀的思想。
神经衰弱者在傍晚的时候与他的医生朋友在疗养院的林荫道上散步,遇上一个叫白雪球的漂亮女人。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在她留下的香风里,医生对神经衰弱者讲了关于这个女人的故事:一天早晨,老男爵来到医生这里,询问他的血液里是否真的含铁,是否可以提炼出铁,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找到一位化学家,要求化学家抽出他的血并从中提炼出35克铁。老男爵的理由是,他太爱白雪球了,他已经给了她所梦想的一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以一种物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一次性地把他的骨髓和血液中残留的一切都交给她,那是他的全部实体。两个月后,化学家交给男爵一小块铁。男爵为它的小而深感失望,但想到白雪球会因为拥有这样一件首饰而高兴得哭泣,他也就安慰了。几天后,奄奄一息的男爵把白雪球叫到身边,把这枚铁戒指套在了她的手上:“白雪球,为了提炼这些铁,人家挖开了我的血管……我把自己弄垮了,为的是能让你拥有一只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曾经拥有过的戒指……你觉得幸福吗?”白雪球略含轻蔑地看了一眼那只戒指,然后非常实在地说道:“啊!老朋友……你知道……我倒更想要一只座钟。”
在医生的大笑中,白雪球的香风消失了。然而,这实在是一个不好笑的故事。
悲哀像渐渐袭来的夜幕,包围了暮色中阅读的人。男爵的痴情和愚蠢,女人的冷酷和贪婪,都令人透不过气来。世间有谁能像男爵这样无边地去爱?可是他全部的心血为什么打动不了别人?他是想过要送白雪球一个金戒指的,可他的血液里不含金,不是他身体里的一部分,他又觉得无意义。可叹他全部的实体最终也还是没有落实到意义上,可见意义并非来自身体的内部。
当我试图把自己的思绪清理出一个脉络,落实在纸张上,我想起了母亲留给我的那枚金戒指,已经4年了,它一点也没有改变。它不是母亲体内的东西,但我能从那上面读出母亲全部的信息,它是情感和意义的凝聚之地。它在属于母亲之前,在商店里,在加工车间,它最早是在矿地,是母
亲的手指赋予它一种意义,所以它在我手上时,我感到一种安慰的满足。
现在该好好想想爱这个问题,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断很多很精彩,可我竟
然一句也说不出。记忆的衰退似乎更能提醒爱的可贵,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用来爱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其实更应警醒的是怎样去爱。父母之于子女,男人之于女人,朋友之于朋友,爱与被爱,都有一个尺度和一种精髓,有一语中的的表达,也有心领神会的沉默。多年前的一首流行歌曲曾经唱道:“我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爱你……”是啊,难道那个老男爵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吗?那是独一无二的方式,为什么那样心血的奉献换取的是冷漠?爱要有悠长的回音才有意义;爱是两端平举的绳索,不可倾斜;爱由最平凡的举动一点点组成,没有惊世骇俗可言。事实上,我们这些现代人,这些比过去更多地谈论爱的人,同样在犯着爱的错误。
一切由爱产生的悲哀,在于爱与被爱的失衡。
平衡的爱,一枚草戒指足以保持平衡。
那枚荒诞的铁戒指离我们已有一百多年,但它清冷的光辉一直在延伸,延伸……